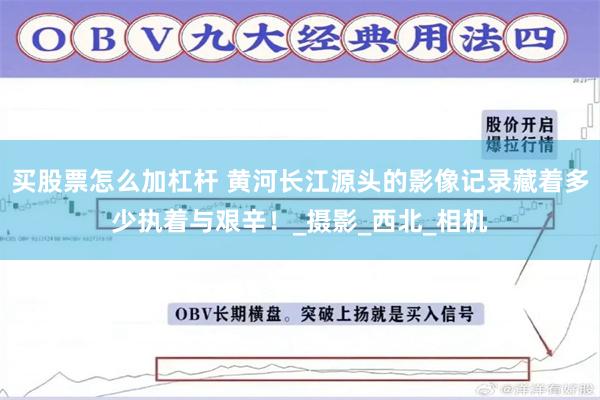
人民画报社离休干部、著名摄影家、高级记者茹遂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买股票怎么加杠杆,享年92岁。
茹遂初在北京家中,2013年 袁毅平 摄
茹遂初一生致力于国际传播事业,70余年的摄影生涯里,他亲历了青海土改,先后倡议和参加了黄河、长江源头的摄影采访,曾多次探访丝绸之路,深入全国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进行专题摄影报道,并在摄影出版、展览等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是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的践行者。他曾获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创作的大量记录新中国建设、文化与民生的摄影作品与专题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深受广泛赞誉,作品先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收藏。近年来,茹老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扫描整理自己在上世纪拍摄的老照片,他努力通过不同方式使这些承载历史信息的老照片得以保存和传播。
2022年至2024年,《中国摄影》编辑曾对茹遂初进行过数次采访,并对他的口述文本进行了整理,最终稿件以《为时代存真,为百姓留影》之名,发表于7月刊“档案”栏目。我们节选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以此来纪念茹隧初为摄影事业所奉献的一生。
展开剩余95%第一次拿起相机拍照
1932年我出生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家人回到原籍陕西三原县。
1949年家乡解放后不久,我就在西安参加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先后做过誊写员、生活干事、编辑,后来领导又安排我做了文字记者。那时,西北总分社总编辑林朗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几台东北总社赠送的日本老式相机和两台苏联相机,高兴地说,有了照相机,我们也要搞新闻摄影。那时候只有编辑部的秘书黄修一略通摄影技术,领导便委派他为摄影科科长。摄影科成立了,需要工作人员,我便鼓起勇气找林朗谈了想学习摄影的想法,林朗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对我说:你可别干几天就不干了。我回答说:不会的。就这样,两三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我在事业上的“终身大事”,从此便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一辈子!
茹遂初,1952 年摄于西安,时任西北新闻局摄影记者
我和摄影科新来的几位年轻人一样,之前都没有摸过相机,学习要从零开始。黄修一给我们讲了摄影常识,并交给我们一台相机去实习。那是台日本老式的胶壳120相机,里面装的不是胶卷,是缠在胶卷轴上的放大纸。黄科长对我们说:“拍摄时曝光时间长一点,显影后放大纸上会形成负像,体会体会就行了,别浪费胶卷。”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摄影记者”很快便装备起来,有了一台像样的照相机,便开始进行摄影采访活动。尽管当时登在报纸上的照片影像不那么清楚,但毕竟是一个新的开端。
亲历青海民族地区土地改革
1950年,西北新闻局成立,原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摄影科划归西北新闻局,以便和新闻总署的新闻摄影局对口。1951年上半年,组织安排我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半年左右的干部轮训,结业后学校抽调了大约300名学员组成土改工作团,前往青海支援那里的土地改革。局领导林朗要求我除参加土改工作外,还要担负土改的摄影报道,并亲自出面请西北土改委员会给青海土改委员会写了一封介绍信。就这样,我以土改工作队员和西北新闻局摄影记者的双重身份,在青海的民和县、湟中县先后参加了三期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这种双重身份与单纯下去采访有所不同,我随身带着照相机,作为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员,天天和农民在一起,而不是旁观,因此对土改的认识和感受可能更直接一些,观察可能更细致一些,对农民感情的体会可能更深刻一些。
土改中贫苦农民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青海,1951年 茹遂初
那时我随身带着相机,参加土改各项工作,随时将我认为有价值的镜头和使我激动的场面拍摄下来。1950年代初,胶卷来之不易,为了节省胶片,一个镜头我一般只拍一张,拍两三张的很少。有时也会失去一些镜头和拍摄时机,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在镜头的选择和画面处理上考虑得更仔细些。这批土改的片子,除在《西北画报》发表外,底片全部归档由画报社资料组保存,我手头一张也没有。
10多年前我买到一本国外以编年史的方式出版的《世纪》大画册,我翻阅时在“1951年”这部分看到一张有关中国的照片特别眼熟,仔细一看,是我当年在青海拍的一张土地改革的照片!这张照片引发了我寻找这批土改老照片的念头。《西北画报》撤销后,部分编采人员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筹建《民族画报》,我想,原《西北画报》的图片资料移交民族出版社的可能性较大,便托民族画报社当时的总编辑车文龙帮我打听,很快就得到他肯定的答复:这批图片资料还在。当我在民族画报社的资料室,看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资料册和底片夹时,感慨万千。非常感谢民族画报社的支持,使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得以重见天日。
民和县一区二乡在土改中用没收地主的财物举办实物展览,以教育农民。青海,1951年 茹遂初
2006年《大众摄影》杂志社以“曾经的岁月”为题最先在“大众影廊”部分展出了这批土改老照片,随后一些媒体也分别作了专题介绍。2014年新浪网图刊“记忆”以《亲历中国土改》为题发表了27幅土改老照片,网友的反应强烈,两三天的时间,就有成千上万的网友留言。我所拍摄的这些土改老照片在拍摄手法上都是记录式的,并无独到之处,有些照片甚至连焦点也不实。我想,只是这些真实地记录当年土改的老照片所传递的具象历史信息,有助于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对土改回顾和思考,也有助于未曾经过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对土改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引起网友的关注和兴趣。
青海民和县川口区第二乡的农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选举农民协会委 员,坐在前排的是候选人。青海,1951年 茹遂初
1952年我结束青海的工作回到西安时,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创办一本面向少数民族多文种的《西北画报》。原西北新闻局摄影科全班人马成了画报的班底,由黄修一同志担任主编,领导安排我担任记者组组长。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西北画报》也随之停刊。尽管《西北画报》存在了不到两年,但却让我的记者生涯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转向图文结合的专题摄影报道。1954年10月来我调到北京,在人民画报社继续从事摄影记者工作。
为了防治绵羊的寄生虫,牧民在给绵羊进行药浴。青海,1972年 茹遂初
荣誉背后的影像价值
《引洮河水上山》这幅多次获奖的摄影作品是1958年我在甘肃拍摄的。甘肃省历史上以干旱闻名,特别是甘肃中部和东部黄土丘陵地区,更是十年九旱。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甘肃省决定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把洮河水引上山,使甘肃中部1500万亩干旱的土地得到灌溉,还可以发电、行船。十几万农民大军开进崇山峻岭,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改造自然的战斗。1958年12月我接受采访任务,来到工地时,立即为那个年代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更为农民兄弟为改变干旱贫穷面貌所迸发出的劳动热情所感动。
引洮河水上山。甘肃,1958年 茹遂初
拍摄时我采用逆光强化了画面的层次感和气氛,加之劳动时扬起的尘埃,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和气势,我只对个别人物的位置稍作调整,就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幅照片。除了黑白片,同时还拍了彩色反转片。1959年,这张照片先后在《人民画报》、《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同年10月在匈牙利、民主德国举办的国际摄影比赛中接连获金奖和一等奖,其后又在《中国摄影》1957年至1959年优秀作品评选中获一等奖。但引洮工程却未能圆梦。由于决策者的冒进,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两年后,被迫悄然下马。十几万农民兄弟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为之奋斗的梦想就这样付诸东流,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幅摄影作品,与当初拍摄时的愿望相反,成为大跃进年代一曲可歌可泣的时代悲歌。尽管如此,它为那个时代留下一幅发人深思的照片,我想这也正是纪实摄影的价值所在。
深入西藏、新疆的采访活动
我曾于1963年和1965年先后两次去西藏采访。1963年去西藏时,拉萨还未通航,我走的是青藏公路,乘的是后勤部队汽车连运送物资的卡车,因为是集体行动,若有车子抛锚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走走停停,从西宁到拉萨走了10天。那次去西藏主要的采访任务是报道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变化。我先去藏北当雄牧区,采访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赛马会是草原上盛会,牧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时间草原上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帐篷城。我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拍摄了赛马会期间各种活动和牧民生活。当年9月,我去山南乃东县,采访民主改革后西藏农村的变化。凯松乡是原西藏大农奴主旺青格勒在山南的六大庄园之一。我第二次去西藏是1965年,主要任务是釆访西藏自治区成立。我还做了《拉萨在飞跃前进》《翻身农奴喜丰收》《新人·新生活》等反映西藏新面貌的专题报道。那时西藏已通航,从成都到拉萨当雄机场,飞行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从机场到拉萨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
勘查队借用农民空房建立的野外土壤分析工作室。新疆,1957年 茹遂初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新疆独山子矿区的油井。新疆,1954年 茹遂初
新疆是我去过最多的地方。1953年和1954年我还在《西北画报》时就曾两次去新疆采访,对新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调到《人民画报》后,第一次去新疆采访是1956年秋天,任务是采访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在新疆阿尔泰的考察活动。这支队伍有地貌学、土壤学、植物学、昆虫学、农学、畜牧学等学科的五十多位科学家,我随科考队进入阿尔泰山,一直深入中苏边境的喀纳斯湖。科考活动结束后,经领导同意,我继续留在新疆采访。冬天,我和《新疆日报》的摄影记者伊敏尕依提相约,一同乘运木材的卡车进入天山,采访了一组反映牧民冬季生活的专题报道。1957年春天,新疆荒地勘测设计局一支荒地勘查队前往塔里木盆地进行荒地调查,我随队采访,真真正正过了50天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经历和锻炼。《中国摄影》1958年第2期扉页刊登的《沙漠勘探队》,就是这次采访中拍摄的。这也是《中国摄影》创刊后发表的我的第一幅作品。结束塔里木盆地荒地勘查的采访后,我从轮台西南行至喀什,再从喀什东南行至和田,差不多围绕塔里木盆地跑了半圈。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出版的巨型画册《中国》选用我拍摄的照片有14幅,其中不少就是这次在南疆拍摄的。
考察队员穿过芦苇丛前往工作地点。新疆,1956年 茹遂初
伊犁地区的边防战士巡逻在边境上。新疆,1968年 茹遂初
母亲河探源
黄河源头究竟在哪里,过去没有报道过。
1972年上半年,我提出用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设想,得到社领导的支持。据我们所知,当时除1952年一支由部队组成的河源勘查队到过黄河源头外,此后再没有考察队到过那里,更没有关于黄河源头的报道。既然是连载,我主张从源头开始,会更吸引读者。我主动表示愿意承担黄河源头的采访任务。8月底我和编辑贾玉江同志到达西宁后,一方面在青海省水电局的支持下筹备野外生活的必要物资,一方面跑省图书馆查阅历代有关黄河源头的记载。1972年9月13日,配合协助这次黄河源头采访活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和青海水电厅的两位工作人员与我们一起来到黄河最上游的玛多县,在当地政府的热情帮助下,组成了包括5位藏族民兵和一位医生、一位公安干部共12人的河源采访小组。9月18日采访小组骑着马,赶着一群驮运器材装备和给养的牦牛,带着一张1952年解放军河源勘查队绘制的河源地区略图,进入了茫茫的大草原。
茹遂初(左一)在黄河源采访途中,1972年 贾玉江 摄
经过十余日艰苦的行军,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经鄂陵湖、扎陵湖西行经星宿海进入约古宗列盆地,沿黄河源流约古宗列曲西行折而向南,终于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缘,找到了一处从地下涌出的泉水,溢出的泉水形成一条宽不及一米的小溪,这就是黄河源头!这就是1952年河源勘查队确认的黄河源头!为了弄清楚当年地图标示的黄河发源地雅合拉达合泽峰与黄河水系有无关系,我们决定继续西行,并最终登上海拔5214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峰,就我们的观察,它与黄河水系并无关系。我们还在当地了解到雅合拉达合泽藏语无此名,实则系雅拉达泽。
姑娘们参加春节联欢会后走出剧院。新疆,1956年 茹遂初
从内地来到乌鲁乌木生活的姑娘们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烤羊肉串。新疆,1956年 茹遂初
这组反映河源地区自然风貌和牧民生活的专题报道,以《黄河源头行》为题,作为《人民画报》“大河上下”专栏连载的开篇,用8页彩色版发表于1973年第6期。那时画报每期总计只有44页,一组报道给8页篇幅,是极少有的。采访即将完成时,我因马失前蹄,从马上摔下,腰部受伤,因此未能参与连载后续选题的采访,是件遗憾的事情。
再出发:寻访长江源头
在完成黄河源头探访任务后,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重登青藏高原,探寻祖国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探访长江源头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1976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遇,经水电部和报道组的军代表老陈同志介绍,我和长办(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政治部宣传部长程绶台同志就《人民画报》以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长江的设想交换了意见,并得到了双方领导的支持。很快就商定由长办牵头组织这次长江源头的摄影考察活动,为了扩大活动的影响,长办还出面邀请了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参加,后来青海日报也参加了。当时长办主任林一山对长江源头的摄影考察活动也很重视,亲自出面争取到兰州军区和青海军区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
江源地区的气象站。青海,1976年 茹遂初
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自古以来众说纷纭。1974年兰州军区第六测绘大队开始对青藏公路以西广大的“无图区”进行航测和地面作业,但是我们1976年探寻长江源头时尚未出图。江源摄影考察组的专业人员根据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比较各种说法,并参考一张1∶100万的地图和国外出的卫星影像图,依据“河源唯远”的原则,决定把沱沱河的源头作为我们这次摄影考察的目标。
1976年7月21日,我们这支由记者、专业人员和解放军共28人组成的江源摄影考察小组分乘3辆北京吉普和两辆10轮传动的大卡车从西宁出发,翻过海拔4772米的昆仑山口,7月26日到达沱沱河沿,它是青藏公路上的一个居民点。摄影考察组以沱沱河兵站为依据,沿公路两侧进行了数日的考察活动,同时为前往江源进行适应性锻炼。在此期间,有3位同志因高原反应强烈,被连夜送往格尔木。8月12日考察组按计划出发,车子不时地陷入草甸和沼泽地,5天的时间才行走100多公里。由于高原缺氧,汽油超量消耗,如继续乘车前行,进去就有出不来的危险。好在出发之前,我们通过沱沱河当地政府向藏族牧民雇用了马匹。但随之而来一连三天的风雪,按约定送来的马匹在风雪中失散了11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将一部分同志留在大本营,记者和专业人员组成两个小分队,分头轻装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我们这支小分队共8人,任务是沿沱沱河南行,直奔沱沱河的源头,也就是我们当时确认的长江源头。8月23日,我们终于到达朝思暮想的大江之源⸺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峰下的姜根迪如冰川。
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的姜根迪如冰川。青海,1976年 茹遂初
抵达后的第一天是个大阴天,我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选择了拍摄大江之源的最佳角度。8月25日一大早,我钻出帐篷一看,万里无云,雪山、冰川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晶莹的光辉,映衬着蓝天显得格外的壮丽。我急忙扛起器材出发。由于拍摄大场面的角度下午光线效果最好,于是我利用上午的时间拍摄了一些中近景的镜头,临近中午才向预先选定的拍摄位置爬去。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海拔已近6000米,每前进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大气,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事先选定的拍摄地点。
江源地区冰川消融形成的冰洞。1976年 茹遂初
我架起哈苏相机,经过仔细的观察,要表现出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需要拍摄一套四接片。“噼啪”“噼啪”“噼啪”……当我按到第四张的时候,没想到快门按不下去了,啊—片子用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问题,真叫人着急。我赶快换上黑白暗盒拍摄了一套接片,又手持135相机拍摄了几张。高原的气候真是瞬息万变,当我装好120彩色反转片准备拍摄时,太阳已被乌云遮住,一直等到傍晚,太阳再未露面。当我背着沉重的器材下山时,心中的滋味真是难以形容。直到回北京片子冲出来后,效果还不错,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1977年第4期《人民画报》在专栏连载的开篇以跨页的篇幅刊登了这幅表现长江源头自然景观的三接片,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现了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几十年来,这幅照片曾多次为杂志、书籍、画册和网络所采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长江”条目也采用这幅照片作插图。我想这就是摄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体的作用和价值所在。这次考察的成果,确认长江的长度超过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的亚马逊河,为世界第三大河。此后新的出版物都修改了过去的说法。
2010年3月中央电视台10频道“2度计划”摄制组,带着我30多年前拍摄的长江源头的照片,前往江源,在我当年拍摄长江源头的同一视点拍摄了一张对比照片,原本壮丽的姜根迪如冰川消融得只剩下一点残迹。这幅对比照片发布后,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世人的震惊。这使我更进一步意识到我们摄影人有责任为生态环境保护多作贡献。
关于“丝绸之路纪行”
在197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时,就萌发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在画报上开辟专栏连载的想法。因为“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东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和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陆上交通通道,对古代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丝绸之路”逐渐为人们所知悉,并成为古代东西方友好交往的象征。因此,我认为报道古代“丝绸之路”有现实意义,可以做到“古为今用”。“丝绸之路”沿线有关遗迹、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以及沿线的风光、风情,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兴趣。同时也可通过报道反映“丝绸之路”沿线今天的面貌,增加国外读者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了解。1975年,我正式向社领导提出在画报上开辟“丝绸之路”专栏连载的设想,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实现。“文革”后,旧事重提,1978年在社领导兰志安同志的支持下,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采访工作由我和陈和毅、杜泽泉三人分工担任。按计划采访工作在1978年和1979年完成。“丝绸之路”专栏连载从1979年第6期《人民画报》开始见报,共连载了20期。在画报连载的基础上,我又和陈和毅、黄祖安同志合作编著了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丝绸之路》,由人民画报社与法国一家出版社合作,1985年在法国出版发行。
工人们在陡峭的山坡上进行刷坡作业,宝成铁路,1956年 茹遂初
离而未休,创建“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
离休后,我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继续画册的编辑出版,二是牵头创建了“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本世纪初,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网络,将中国知名摄影家特别是老一辈摄影家的作品通过网络集中保存、展示和传播。2005年夏天,我与博客网就在该网图片频道建立“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专栏一事达成协议,并邀请摄影界知名人士和网站工作人员组成编委会。编委会成员包括:袁毅平、柳成行、佟树珩、杨恩璞、郭志全、段继文、蒋铎、方学辉和博客网的冯磊、杨劲奕,大家推举本人担任编委会主任。在博客网和摄影界朋友的支持下,到2006年12月底已有60余位知名摄影家的作品上网。2007年,编委会决定从博客网分离出来,在原专栏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www.fotocn.org),2008年9月6日,网站正式上线。到目前为止,网站已为180余位知名摄影家建立了作品档案,累计拥有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作品数万幅。这些摄影家中有不少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或较大影响,如沙飞、石少华、吴印咸、方大曾、郑景康、庄学本、孙明经、齐观山、钱嗣杰、高帆、蔡尚雄、邹健东、张印泉、陈复礼、简庆福、黄翔、袁毅平、吕厚民、吕相友、朱宪民、王苗、解海龙、许林、翁乃强等,档案网收藏的作品既有摄影家的代表作,也有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作品。
2009年6月中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隆重推出了大型图片专辑《六十年沧桑巨变⸺共和图像记忆片断》,收录将近80位老中青三代摄影家的2000多幅珍贵纪实图片。专辑按年排序,每10年为一个时间段。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民族、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清晰展现出共和国60年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我国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网作为合作伙伴完整地转载了这个专辑。
更多茹遂初作品
交通民警在耐心地回答行人的询问。上海,1964年 茹遂初
上海机床厂青年职工业余合唱队在练习。上海,1964年 茹遂初
敦煌莫高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壁画和彩塑进行摄影记录。甘肃,1978年 茹遂初
南澳岛的海防尖兵。广东,1963年 茹遂初
大连造船厂为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制造的27000吨散装货轮“长城号”下水仪式 。1981年 茹遂初
沈阳工人新村的居民鞠智兴一家。沈阳,1959年 茹遂初
江阴华西村农民的子女,从幼儿园开始即享受免费教育。江苏,1984年 茹遂初
常州灯芯绒厂的工人正在包 装出口产品。江苏,1974年 茹遂初
改革开放中的广州,广州1986 年已有六千多辆招手即停的出租汽车, 使乘车难的问题得到了改善。广东,1986年 茹遂初
茹遂初年表
1932年 生于南京。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回原籍陕西三原县。
1948年 初中毕业,考入三原工业职业学校。
1949年5 月西安解放,同月在西安参加革命,10 月间开始学习摄影,先后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新闻局任摄影记者。
1951年 干部轮训,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约半年,结业后组织安排前往青海民族地区参加三期土地改革,并担负土改的摄影报道工作。
1952年 回西安后参与筹建《西北画报》,任该刊记者组组长。
1954年 大行政区撤销,奉调来京,在《人民画报》任摄影记者直至1993 年离休,其间曾任《人民画报》编委。
1958年 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1959年 作品《引洮河水上山》先后在匈牙利、民主德国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和国际摄影比赛中获金奖和一等奖,其后又在《中国摄影》1957-1959 年优秀作品评选中获一等奖。
1972年 倡议《人民画报》以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母亲河—黄河,并担负“大河上下”专栏连载开篇“黄河源头行”的釆访任务。
1976年 倡议、策划并参与《人民画报》“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釆访,在开篇“大江之源”的报道中,第一次向读者展示了江源各拉丹东壮丽的自然景观。
1978年 策划并参与《人民画报》“丝绸之路”专栏连载的摄影釆访,本年度的釆访活动主要在陕西和甘肃,重点选题有:“古代东方名城—西安”,“丝路明珠”(敦煌莫高窟)。
1979年 继续在新疆进行“丝绸之路”专栏连载的摄影釆访,重点选题有:“火焰山下”,“库车—古龟兹”。
1981年 摄影作品“南疆秋色”(1979 年拍摄于新疆)在东京举行的亚太地区摄影竞赛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奖。
1984年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风光花卉组会员作品展。
1985年 纪念郑和下西洋580 周年之际,为报道“海上丝绸之路”,于3 月29 日至5 月6 日先后访问了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所在国相关部的协助下拍摄了有关海上丝路的遗迹、遗址以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
1991年 策划并主持由人民画报社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合作编辑的大型画册《中囯自然景观》出版发行。
2003年 与五洲传播出版社合作编辑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大型画册出版发行,除中文版外,同时出版有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葡萄牙文版、西班牙文版。
2008年 牵头创办“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并担任编委会主任,目前网站已收藏180余位摄影家的作品。
2014年 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第十届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2016年 摄影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7年 摄影作品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典藏”收藏。
2024年 摄影作品再次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24年 摄影作品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2025年 2月,将毕生拍摄的1775幅珍贵作品电子文件无偿捐赠给中国摄影家协会。
2025年 6月11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本文由李森根据茹遂初口述和文本整理买股票怎么加杠杆,并经由茹遂初本人确认。
发布于:四川省